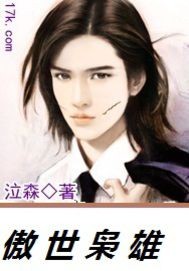眾人不防此變,盡皆呆了。平日裏隻見這章姨父跟著章姨媽,唯唯諾諾,瘟頭瘟腦,屏氣凝神,此刻看他忽然掌摑章姨媽,不免都吃了一驚。
章姨媽亦被打了個愣怔,半晌方才回神,向著章姨父大吼道:“章成儒,你竟敢打我?!你這個濁才料、老殺才、老咬蟲!普天下斷生了男子,我爹娘才會將我嫁給你!你靠著我們母女吃飯,竟還敢朝著我伸手!你再打我一下試試,我今兒不跟你拚了的!”嘴裏嚷著,丟下女兒,就要上來同章姨父拚命。
章姨父人雖窩囊,到底是個男人,被妻子當眾辱罵,自覺顏麵掃地。又見章姨媽撲來,不覺將手一推,便把章姨媽推在地下。章姨媽跌坐在地,更如瘋婦一般,長嘯了一聲,一咕嚕自地下爬起,就要再衝上去。
正當此時,忽聽陸誠勇暴喝一聲:“要打就滾出去打,陸家不是你們撒潑的地方!”
這章氏夫婦還要作態,忽被陸誠勇喝斷,不由盡皆怔了。章姨媽哼了兩聲,向他冷笑道:“我說勇哥兒,你也別衝你姨媽挺腰子。你才當了幾天的官,就在親戚跟前擺起官架子來了!你姨父在外縣做官時,你還不知在哪裏吃奶!你不敬我這個長輩便罷了,也該看覷你表妹一眼。別弄得撕破了臉皮貼不上,咱們各自難看!”她滿以為章雪妍身子已歸了陸誠勇,陸誠勇即便是個不講情義之人,總要顧惜兩份顏麵,以此為脅必定能迫他就範。
豈知陸誠勇哪裏同她女兒有這茬子賬,隻被他們一家三口鬧得氣血上湧,火冒三丈,又聽了她這一番倒三不著兩的話,越發怒了。
當下,陸誠勇更不打話,掄起兩隻鐵壁,將這兩口一手一個,拎起衣領,一徑提到大門上,將手一揚,竟而丟了出去。
這章家兩口跌了個狗啃泥,半日爬不起來,好容易自地下紮掙起身,又滾了一身的土,好不狼bèi。這兩人不曾料到陸誠勇竟能下這等狠手,氣的渾身哆嗦。那章姨媽發了刁潑,更不肯善罷甘休,就要再去尋陸誠勇的麻煩。陸誠勇卻早已關門進去,並吩咐門上小廝將大門緊閉,任憑這兩口如何拍打叫罵,絕不肯開。
這兩人吵鬧了一回,見門裏悄然無聲,並沒半個人出來,隻好作罷。
章姨父便道:“這下可怎生是好,女兒還在裏麵,倒怎麽領她出來?”章姨媽冷笑道:“你還記得有個女兒,我還道你在前堂上黃湯灌的飽了,早已不記得今兒是做什麽來的了!叫我們母女兩個在後院裏,被那小賤人下套擺布,審了又審,險些把一世的名聲都葬送進去!你卻在哪裏?!”章姨父便埋怨道:“我早說這計策不好,你隻是不聽。想陸家的長媳,既然當家做主這些年,家裏家外的操持,什麽人沒見過,什麽事沒經過?那段精明可是白給的?我那等勸你,你隻說萬無一失。如今怎樣?叫人家擺下連環陣候你,把你們母女兩個都裝進套裏。咱們兩個丟臉也罷了,又何苦賠上女兒?”
章姨媽怒道:“你何曾勸我來著?來前在家,你除了去衙門當差,便是同著那班狐朋狗黨出去胡天胡地,又吃又賭。我要尋你說句話也沒處兒尋去!弄到如今,見事情不成了,又來放這馬後炮!”章姨父說她不過,又素來低頭下氣慣了,隻問道:“說這些個也是無用,女兒還在陸家,倒怎生處?”章姨媽譏諷道:“你也不用焦急,左不過一會兒就送還回去了。你還指望,他們留著雪妍過年不成?”說著,又咬牙切齒道:“往昔隻看姐姐來信,原道勇哥兒是個重情重義的。誰知這天下烏鴉一般黑,原來也是個穿上褲子就翻臉不認的,你們男人都是一個德性!既然這等,趁著女兒傷重在他家裏,索性一不做二不休,到衙門告他們一個逼淫婦女的罪名!我看他這三品大員還有沒臉麵做下去!”
她越說越怒,全不細思,逼著章姨父即刻就要到衙門去鳴冤告狀。
章姨父卻道:“你昏了頭不成,且不說今日這事兒沒頭沒腦,其內情形究竟如何,你我一概不知。就是女兒當真同這陸誠勇有了私情,他如今已是正三品的武將,又得皇帝青睞,正是如日中天的時候。俗話說官官相衛,那些老爺們自然都是向著他的。咱們平民之家,怎能同他鬥?不如還是先回去,待女兒回來,問過了再做打算。”章姨媽本自有些城府心機,適才不過是怒極之言,聽了丈夫一席言語,怒氣漸消,也就不再言語,跟他一道乘車歸家。
卻說陸誠勇被章姨媽一番言語激怒,將他夫婦二人扔出門去,就向著門上小廝吩咐道:“往後再不許這家人上門走動,誰若放了他們進來,得我打聽出來,必定打斷他狗腿!”眾小廝突見少爺如煞神一般,將太太的親戚提了扔將出去,各自嚇得魂不附體,慌忙應下。
陸誠勇交代門人已畢,轉身走回上房。進門便見柳氏在圈椅上坐著,兩隻眼睛紅腫,抽噎個不住,見他進來,越發大聲泣涕起來。
陸誠勇隻作不聞,四下看了一回,並不見父親陸煥成,遂走到夏春朝跟前,低聲問道:“老爺哪裏去了?”夏春朝答道:“老爺說堂上有客未去,不好讓人家空坐,就先去陪客了。”說著,又輕聲淺笑道:“你也去罷,這裏有我呢,不妨事。”陸誠勇聽聞,不置可否,隻往床上看了一眼,卻見章雪妍仍未醒轉,聲息不聞。
夏春朝順著看去,心裏會意,冷笑點頭道:“你去就是了,這裏交給我。”陸誠勇點了點頭,這方轉身抬步出門。
柳氏不料兒子自進門來再不曾看自己一眼,隻同兒媳說了幾句話就又去了,不覺又氣又恨,愈加放聲大哭。
夏春朝卻不加理會,隻吩咐丫頭道:“說了這一日的話,好不口渴。到房裏往我揀妝裏取毛尖來,叫寶兒燉一盞來吃。”珠兒應了一聲,就要出門。那迎夏乖覺,連忙上來笑道:“奶奶要吃茶,太太房裏有極好的六安茶,我去燉與奶奶吃,不必叫珠兒姐姐又走這一遭。”
夏春朝卻不言語,將她從頭到腳看了兩遭。迎夏被她瞧的遍體生涼,強笑道:“奶奶隻顧瞧我是怎的?”夏春朝搖頭淺笑道:“好一個伶俐丫頭,不枉了太太這般抬舉你。然而你點的茶,我可不敢吃,誰知裏麵有些什麽。”迎夏聽聞,便知那事是弄穿了,陪笑道:“奶奶說笑了,我縱然粗苯,點個茶還是能的。何況茶裏還能有什麽,左不過是茶葉、紅棗,就是水講究些,奶奶平日裏愛個什麽口味,告sù我一聲便是。”夏春朝笑而不語,仍舊吩咐珠兒道:“你快去,我如今吃個茶也這樣難了。”珠兒笑了笑,轉身快步出門。
那迎夏碰了個軟釘子,臉上便很有些訕訕的。夏春朝正眼也不瞧她,徑自走到柳氏跟前,張口說道:“太太省些力氣罷,橫豎看戲的人都去了,這又是做給誰看呢?”柳氏哭聲戛然而止,抬眼瞪著夏春朝,咬牙恨恨道:“小蹄子,這下可趁了你的心!能挑唆的勇哥兒六親不認,遍天下也尋不出你這樣的好媳婦來!”
夏春朝於她這番言辭早已膩煩,隻淡淡說道:“便是我將少爺挑唆到這般的,太太又能如何?”柳氏不料她竟當麵認了,登時一怔。隻聽夏春朝道:“似章家這等不知廉恥、扭股糖一般的親戚,我連見一見都嫌髒,真不知太太看上他們哪些?就是當個叫花子來打發,也要看他們配不配。縱然表妹是太太的外甥女,一雙手還要分個手心手背,誰家的婆婆如太太這樣裏外不分的。太太且好生想想,不要這等不知高低,往後多少好日子呢,別自家攪的家反宅亂起來。”說著,頓了頓,又道:“表妹在太太這裏不方便,我那裏倒是清淨。我先帶表妹過去,待她醒來,我自然安排妥帖人送她回去,太太不必掛心。”一言未畢,當即吩咐人抬了春凳上來,要將章雪妍挪過去。
那章雪妍如死人一般,僵臥榻上,任憑搓弄。柳氏欲待上來阻攔,奈何他們人多勢眾,又皆聽命於夏春朝,無力阻擋之下,隻好眼睜睜看著一眾人簇擁著章雪妍去了。
夏春朝臨出門之際,忽想起一事,轉身向柳氏笑道:“有句話要叮囑太太,一時隻怕忘了。這手腳不幹淨的奴才,不能放在家裏,早些打發出門,也免日後的禍端。”說罷,望著迎夏一笑,徑自出門去了。徒留柳氏主仆兩個,坐在堂上,罵不絕口。
夏春朝吩咐人將章雪妍抬回房,放在屋中地下,便揮退了眾人,隻留兩個丫頭在屋中伺候。
她放著章雪妍先不發落,走回房中換了家常衣裳,梳頭勻臉已畢,寶兒將茶送了上來。夏春朝接過茶碗,在炕上坐了,一麵吃茶,一麵向兩個丫頭道:“今兒請的客人實在多,人多手雜的,不知還有沒有旁的什麽毛賊,進來渾水摸魚偷了什麽去,記得待會兒叫你旺兒嫂子仔細盤查盤查。”她意有所指,那兩個丫頭又豈有聽不出來,會意一笑,皆不言語。
夏春朝吃了兩口茶,又說了幾句閑話,隻是不提如何處置章雪妍。寶兒終究老實,憋不住便問道:“奶奶,章姑娘還在咱們堂上躺著,奶奶預備如何?”夏春朝杏眼一抬,微微一笑,說道:“讓她躺著去,急什麽?”珠兒在旁插口道:“隻怕待會兒少爺就回來了,表姑娘在外頭橫著,倒礙了少爺同奶奶說話。”夏春朝這才笑道:“這倒是,我險些忘了。”說著,將茶碗往炕幾上一撂,吩咐了一句“去提一桶冷水來。”便抬身向外去。
寶兒不明所以,隻是依言辦差。珠兒卻已然明了,嘻嘻笑著,隨夏春朝出去。
待這主仆二人走到堂上,隻見章雪妍照舊躺在春凳之上,雙眸緊閉,聲息俱無。夏春朝在椅上坐了,向珠兒問道:“這表姑娘也昏了許久了,怎麽還不見醒來?”珠兒掩口一笑,說道:“想必姑娘適才撞狠了,要下一貼猛藥才能醒轉呢。”夏春朝恍然大悟道:“原是這樣,卻才被姨太太兩口子一通亂鬧,我卻把這事給忘了。表姑娘今日被人指證與人私通淫奔,以死明誌撞了腦袋呢。”她口裏說著,一雙杏眼望著下頭,果然見章雪妍身子微微發顫,不禁又是一笑。
便在此時,寶兒提了水桶進來,說道:“奶奶,水取來了,做什麽使?”夏春朝向著珠兒一努嘴,珠兒會意,連忙走下去接了水桶,含笑說道:“你歇著去,我來。”
寶兒退到了一旁,珠兒走到春凳旁,雙手一翻,便將整桶冷水全澆在章雪妍頭上。
章雪妍躺在凳上,耳裏聽著這主仆兩個說話,正不知所以,忽被兜頭澆了一桶冷水,再裝不下去,隻好爬起身來,怒視著夏春朝,麵露猙獰之色,咬牙道:“夏春朝,你竟這等辱我,未免欺人太甚!”
夏春朝淺淺一笑,說道:“倘或章姑娘安分守己的待在自己家中,我要欺你還沒處兒欺呢。你今日是自討其辱,又能怪誰?!”章雪妍額頭紅腫,麵有血汙,遍體濕漉,狼bèi無比,向著夏春朝憤憤道:“今日之事,你我心知肚明。我自來就不識得什麽張二,亦不曾去過什麽西北大營,你如此構陷於我,心腸狠毒如斯,不怕遭報應麽?!”
夏春朝冷笑道:“你身為朝廷在冊的節婦,卻來勾引有婦之夫,若這世上真有什麽報應,就該第一個應在章姑娘身上才是。今日你做了些什麽好事,你自家心裏清楚。我也當真是不能明白,一個未出閣的姑娘,怎麽就能下賤到這個地步。你守不守節,與人無幹。若是你為身後倚靠打算,再要嫁人,世間男子頗多,你嫁誰不可,為何定要黏著我家相公?你既欺到我頭上來,我自然不能容你。我本意隻是將你趕開便罷了,誰知你今日自家送上門來。你既然自願受辱,我又何必同你客氣?”說著,她星眸一轉,頷首笑道:“是了,想必章姑娘是聽信了我家太太的言語,自謂進了陸家的門,便可當上個二奶奶,好坐享富貴了。隻可惜姑娘被奸人糊弄了,陸家外頭我不敢說,裏麵卻是我當家。別說我家相公絕不肯要你,便是納你進門,你也要日日來與我磕頭請安,給我當奴作婢。你道可有翻身的時候麽?章姑娘既然這等愛財,不如回去掛了牌子,倚門賣笑,財路倒還更廣些。依著章姑娘姿色才智,賺取些花粉錢,想必不是什麽難事。”
章雪妍被她這一通言辭,羞辱的氣血上湧,眼前金星亂飛,渾身顫抖不住,好半日才咬牙道:“你不過一個商戶女兒,仗著有幾個錢,才有今日的光景,又有什麽可得意的!”夏春朝點頭笑道:“然而這個商戶女兒就憑著銀錢踩著你的頭,你又能怎樣?我雖是商戶女兒,卻還知道禮義廉恥四個字怎麽寫。想那書香門第的小姐,希圖人家錢財,自貼皮肉,甘願做妾,那才真叫下賤呢。”
章雪妍緘默不言,夏春朝又道:“姨太太兩口都已被我相公打發出門了,章姑娘既然醒了,不如也去罷,留在這兒也是自討沒趣兒。”說著,又吩咐左右道:“拿條手巾,給姑娘擦擦臉。還有大夫開的治心病的藥,也叫姑娘拿上。”珠兒聽聞,便走去拿了條幹手巾出來,連大夫開的兩劑藥一並交予章雪妍,又向她笑道:“姑娘好好揣著,別掉了。這可是治姑娘毛病的良藥,我們奶奶心慈,曉得姑娘家裏一貧二白,差不多就要討飯吃了,已替姑娘付了藥錢,姑娘可別辜負了我們奶奶的一番心意。”
章雪妍今日迭逢驚變,至此時已是心神不寧,又被個丫頭譏諷,隻覺那字字句句皆化作刀劍直戳心肝,不由身子一晃,又險些栽倒。
珠兒向旁一躲,怪叫道:“姑娘可站穩了,別一時跌死了,又怪在我們頭上,我們可承受不起。”夏春朝自覺今日已捉弄夠了章雪妍,也恐逼得狠了,惹她狗急跳牆,便道:“行啦,你既知表姑娘有病,就替她擦擦又何妨。快些替她收拾了,打發姑娘出門,時候不早了呢。”珠兒得了吩咐,笑嘻嘻道了聲“是”,便將手巾扯過來,與章雪妍胡亂抹了兩把。章雪妍立著也不動彈,任她施為。
夏春朝在上頭看著,又向章雪妍笑道:“本該與你換件衣裳,然而我是個婦人,衣衫不合。我家姑娘倒有兩件舊衣,隻怕玷辱了表姑娘,想來姑娘也看不上,就這般湊合著去罷。”章雪妍咬牙道:“不勞費心!”一語畢,便扭身要走。臨出門時,夏春朝忽又冷冷出聲道:“還告sù章姑娘一句話,你既是在冊的節婦,自家就該檢點些。我雖沒讀過幾本書,卻也知道,這節婦再醮,是要吃官司的。”章雪妍步履微頓,卻也不曾再多言語,出門而去。
珠兒上來收拾地下,又問道:“奶奶就這樣輕yì放她去了?當真是便宜了她!”夏春朝歎氣道:“不然怎樣呢?今兒她也算吃了大虧了,張二那事兒本就是假的,當真扭到官府去,弄穿了幫反倒不美。不如就這麽含混著,倒說不清楚。”說著,又淺笑道:“自今日起,她的好名聲就要傳遍京城了,我倒要瞧瞧,我的好婆婆還有沒有那個臉,把這個千金小姐納進門來!”
主仆兩個說了一回話,珠兒忽然想起那張二,便問道:“奶奶,張二那廝要怎生處置?雖說是奶奶安排的,但合家人眼裏,他可是當真偷了咱家的東西。”夏春朝淺淺一笑,吩咐寶兒另端了盞茶上來,細細吃了兩口,方才說道:“將他放了就是,不必多做理會。”珠兒詫異道:“這般處置,奶奶不怕日後難管人麽?”夏春朝促狹一笑,說道:“這怎會呢?咱們這是為了表姑娘名節著想,寧可自家吃虧,息事寧人罷了。”珠兒會意,也跟著一笑。
少頃,夏春朝又道:“你去傳話,就說我吩咐的,即刻將這張二放了。為免人嚼舌頭,叫他自東角門出去。再叫旺兒把丁小三提到二門上,打上三十板子,攆出門去。”珠兒答應著,就往外走,才到門上,就見王丟兒往這邊來,便回身道了句:“夏大奶奶來了。”又向王丟兒笑道:“大奶奶來看我們奶奶?倒也來的巧,那個什麽表姑娘才去。若是大奶奶早來一刻半刻,還不好說話呢。”王丟兒知這是小姑子身前侍奉的紅人,忙拉著她的手笑道:“幾年不見珠兒姑娘,倒出落的這般水靈,跟條水蔥似的,又這等會說話,怪道你們奶奶疼你。”珠兒知曉這王丟兒是個囉嗦的脾氣,不欲同她多纏,虛應了幾聲,便抽身去了。
夏春朝見這嫂子進來,心裏方才想起她還未離去。
原來夏家父子尚未動身,王丟兒自然不能先走,又因上房裏大鬧了一場,不好久坐,她無處可去,自然還隻能來尋夏春朝。
夏春朝經了這一日辛勞,早已有幾分疲乏,然而親戚麵上,心中縱然不耐還是陪笑相待,說道:“嫂子來了,適才我忙著招呼親戚,倒空了嫂子,嫂子勿怪。”一麵說,一麵就吩咐寶兒設座上茶。
王丟兒在下頭坐了,又連忙說道:“哪裏,我知道妹妹事多,哪裏敢怪?也多虧了妹妹這樣能幹,這些事才能這等井井有條。若是換了旁人,還不知怎樣熱亂。”夏春朝曉得這是奉承之言,聽在耳裏倒也受用,當下一笑,同她敘些寒溫閑話,又問道:“一日裏隻顧忙亂,倒忘了問,家中如今怎樣?父親身子可還硬朗?哥哥同行哥兒還好?哥哥是跟著父親在鋪子裏做買賣,行哥兒倒做何營生?”王丟兒忙答道:“叫妹妹記掛了,家裏一應都好。老爺身子康健,日常沒病沒痛的,我同你哥哥還籌謀著老爺今年的五十大壽。到時候,妹妹還上門走走。”夏春朝一笑,說道:“那自然是要去的。”
王丟兒又道:“行哥兒仍在學裏讀書,因他有個秀才功名在身,老爺的意思叫他再進一步,也算光耀門楣了。橫豎家中不缺衣食,也供得起。”夏春朝點頭道:“父親主張的有理,咱們家幾代商戶,好容易出了個讀書的苗子,不要埋沒了才好。聽聞今歲三月,聖上喜添一子,有意加開恩科,這倒是難得的機遇,叮囑行哥兒上心些。若錯了過去,又得熬上三年了。”王丟兒道:“妹妹說的是,老爺也是這麽說呢。”說著,又諂媚笑道:“得行哥兒考了功名做了官,也是妹妹你的臉麵。你在婆家,也更光彩些。”
夏春朝聽了這話,隻覺不耐煩,就說道:“這倒不勞嫂子操心,我原也不靠這個。”一語未畢,便岔了話頭問道:“哥哥同嫂子近來怎樣?自上次嫂子小產,也有一年了,還沒個消息麽?”王丟兒聽問,臉色頓時垮了下來,低頭囁嚅道:“我心裏也急,吃了許多藥,隻是不見個效驗。你哥哥雖不曾說什麽,老爺倒是問過幾次,我空自著急,也沒什麽法子。”夏春朝往日也風聞了幾句,然而子女命數,非人力可為,她亦無別法,也隻好勸道:“嫂子權且寬心,白著急也不是個法子,反倒焦壞了身子。子嗣一事原是難說的,父親當初有我哥哥時,也將二十五六了。嫂子同哥哥也還年輕,想必過上兩年也就好了。”王丟兒卻苦著臉道:“我隻愁你哥哥等不得,這兩年就要弄人進去了。我好容易才把娘家帶來那兩個小蹄子配了人,又怎能容他再弄些狐狸精進去氣我?妹妹若是見了你哥哥,倒是替我勸勸。”
夏春朝卻道:“嫂子這點大可不必憂慮,夏家並無這樣的老例。就是當年我母親嫁過來,一連五年未曾有孕,我父親也並未納妾蓄婢。若是哥哥要壞門風,想必父親亦不會答應。嫂子自管把心放進肚裏,安心調養身子才是正理。”
這姑嫂二人說了一回話,外頭便有人來報,稱夏家父子已然動身,要奶奶也收拾了快去。王丟兒聞言,連忙起身,借夏春朝的妝奩理了衣裝,便起身去了。夏春朝親自送到院門上,看她走遠,方才回去。
再說那章雪妍自出了夏春朝的院子,走到門上一打聽,方才知曉父母已然離去,雇來的馬車自也去了。她在內堂演繹的故事已然不脛而走,陸家家人皆鄙夷她無德淫蕩,也無人理她。她無法可施,隻好又走回上房。柳氏厭恨她無用,又拖累自身,吩咐了丫頭不放她進屋。章雪妍在門上苦求了半日,柳氏方才與了她一錢銀子,令她雇轎子回去。
這章雪妍乘興而來敗興而歸,一份便宜也不曾撈到,反倒討了一場羞恥在身。她這一日擔驚受怕,白受了些皮肉之苦,又被潑了一身冷水,兼且憂心如焚,那嬌嫩的身子如何受得了這等磨折,歸家便大病一場,足足半個月不能下地。自此往後,章家更將夏春朝恨入骨髓。
陸家擺酒忙碌一日,直至日西時分,賓客方才散盡,眾家人人困馬乏,疲憊不堪,此節也無需細述。
陸誠勇送走了客人,回至房中,卻見丫頭寶兒正在門上守著,便問道:“你們奶奶呢?”寶兒向裏麵指了指,又擺了擺手。陸誠勇心下會意,亦不多說,親手打了簾子,邁步進門。
進得室內,果然見床上紗帳半垂,夏春朝臥於其上,蓋著一床紗被,枕上烏雲散亂,一雙雪白的臂膀露在外頭,雙目微闔,桃腮帶赤,香夢正酣。
陸誠勇見此情景,料知妻子忙碌一日,必定神乏力疲,倒也不去吵她。隻微微一笑,出門吩咐丫頭打水梳洗已畢,脫了衣裳,鑽進被內,摟著妻子就要同夢周公。
熟料夏春朝尚未熟睡,被他這一陣揉弄,不覺星眸驚閃,醒轉過來,睜眼一看見是他,不由笑道:“幾時回來的?一聲兒也不言語,倒嚇了人一跳。”陸誠勇攬著她腰肢,一手揉搓著掌下細嫩的皮肉,一麵笑道:“才回來,看你睡著,不想吵你,誰知你還是醒了。”夏春朝睨了他一眼,嗔道:“不想吵我,還是要作弄,生生把人弄醒了,又來說這話。”陸誠勇笑了笑,說道:“想到月底就要離家,我心裏就舍不得,隻想同你多親熱親熱,好一慰離別之苦。”
夏春朝聽出他弦外之音,連忙捉了他的手,說道:“白日裏你弄得過了,我到這會兒腰上還酸,今兒是委實不成了。你平素隻叫我將就你,你也將就我一回罷。”陸誠勇懷裏摟著她軟玉一樣的身子,耳裏聽著她鶯鶯聲軟,眼裏瞧著她那求饒的嬌嫩模樣,縱然心中發癢,卻也舍不得她委屈,當下笑道:“我有說要怎樣麽?瞧把你嚇的,原來你相公這等怕人。”
夏春朝便斥道:“把人奈何成那個樣,就是個鐵打的娘子也挨不過你,如今又來說這便宜話了。”陸誠勇得意非常,翻身將她壓下,低低笑道:“果真如此麽?今日就罷了,明兒我可是要驗的,你若說謊,我可不饒你。”他興致已濃,夏春朝豈能察覺不出,麵紅耳赤之下,啐了一口道:“我不聽你這葷話,你放我起來,咱們正正經經的說話。”陸誠勇還要磨蹭,倒惹夏春朝羞惱起來,斥道:“你再要混鬧,今兒就到外頭炕上睡去,我這屋裏不留你。”陸誠勇這才放手。
夏春朝披衣下床,走去了倒盞茶吃。陸誠勇便坐在床上,雙手環抱,哼哼道:“如今新興的,相公同娘子歡好,要先請旨上奏,不然便不能行。娘子這閨房嚴令,倒比軍規還更嚴苛些,叫我那些同僚聽了去,還不知怎麽笑呢。”夏春朝瞥了他一眼,說道:“誰叫你要同他們說,你自討的倒賴我。”陸誠勇拿她無可奈何,隻好軟磨硬泡的賠不是。夏春朝不理他這些,隻說道:“有件事我倒要告sù你,丁小三我已打發了,他是太太領進門來的,明兒若太太問起來,你去同她回罷。有日子沒到鋪子裏去了,我明兒要去瞧瞧。”
陸誠勇見她說起家務,隻好將放浪之態盡皆收了,點頭道:“今兒那件事,那張二是你找來的?”夏春朝料知瞞不過他,索性告sù了一遍,又道:“那個張二,原是賭場裏的一個搗鬼。今年正月上,他在外賭錢賠了,險些叫那放貸的打死。還是夏掌櫃看不過,替他還了錢,那債到現下不曾還清,故而他不敢違背我的吩咐。”陸誠勇說道:“原來如此,我說這丁小三才與我下藥,怎麽轉頭又去替表妹偷遞財物,卻是你做下的手腳。適才在太太房裏聽你說,當著人前我也沒問,原來有這個緣故在裏頭。”
夏春朝聽他這口氣不好,眼眸一轉,便含笑問道:“怎麽,心疼你那表妹?”陸誠勇笑了笑,說道:“你別胡想,哪有此事。”夏春朝點頭道:“是我胡想,還是你心裏有鬼?我是設計她了,你待怎樣?若不是她硬要來惹我,我也不會與她這場難看。你不去說她不好,反倒來派我的不是?”陸誠勇歎道:“我並沒說你有什麽不是,隻是這手段未免太烈了些。今日這事兒一出,表妹的名聲是必定毀了。她往後在京中要如何立足?”
夏春朝似笑非笑道:“她如何立足,同我有什麽相幹?”陸誠勇望著她不言語,半日才道:“幾年不回來,你的性子倒是有些改了。”夏春朝頷首微笑道:“往日合家子都說我性格軟和好說話,所以才讓家裏生出這些奇談怪聞來。弄到現下,連個外八路的親戚都能欺壓到我頭上來了,我再不立起來,還指望往後在這家裏待下去麽?”說著,頓了頓,又道:“我算看明白了,你同他們也是一樣的。求著我的時候,千也說好萬也順遂。但有半分不順意,就要擺出臉色來與我瞧。自今兒起,我誰的臉色也不看了。你當你的官老爺去,我不伺候!”一語畢,她便上前扯了枕頭被褥,就要往外走。
陸誠勇連忙拉住她,問道:“你哪裏去?”夏春朝說道:“你在這屋裏,我同珠兒寶兒她們睡去。”陸誠勇又氣又惱,扯著她不放,說道:“我何曾說你什麽來著,你就要這樣。”夏春朝道:“你嘴裏不說,你心裏想,不然也沒那些話說了!”
原來,今日出了章雪妍一事,夏春朝足足一日都在氣頭上。若論往常,她也斷不至此。然而今日陸家眾人連著那章雪妍將她激的惱了,直至此刻氣尚不曾消。又看丈夫說話不稱意,肝火越發旺盛。
陸誠勇再不曾見過她這個樣子,本性不善言辭,不知如何是好,隻攔腰一抱,將她拖上床來,壓在身%下,怒道:“你是我娘子,做人娘子的,哪有把相公撇下守空房的道理?!”夏春朝亦怒不可遏,口不擇言道:“既是這般,這娘子我也不當了,明兒咱們就散!”。